文/本刊記者 丁 蓉
不同于外來的專業(yè)攝影師,這些來自鄉(xiāng)村的攝影師們平時或忙于地里的農(nóng)活����,或忙著養(yǎng)雞�����、喂豬���、放羊��,或忙著打工養(yǎng)家�����,很多照片都是他們利用零碎的空余時間拍下的���。
他們用自己的視角,展現(xiàn)他們的生活和故鄉(xiāng)��,記錄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和質(zhì)樸的自然保護觀��,以及他們對環(huán)境變遷的擔憂與展望�����。

雅安鄉(xiāng)村攝影師拍攝的作品—《家鄉(xiāng)的水庫》(攝影/石來)
竹林中生病的大熊貓;站在坡上高歌的村民��;拿著豐收的蕎麥開懷大笑的大媽……
郭思宇傳給記者的圖片集����,透露出濃濃的鄉(xiāng)土氣息��。
這些照片出自四川雅安4個山村12位村民之手�����,是“鄉(xiāng)村之眼—雅安大熊貓遺產(chǎn)地紀錄行動”的一部分成果�����。這些農(nóng)民大多數(shù)是第一次接觸相機���,卻從各自“司空見慣”的農(nóng)家生活場景中��,完成了一次大熊貓棲息地百姓的主動表達���。
“鄉(xiāng)村之眼”是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簡稱“山水自然”)在中國西部開展的一個公益影像計劃,郭思宇是項目團隊成員之一。據(jù)他介紹���,鄉(xiāng)村攝影師培訓計劃的本意���,是通過照相機的鏡頭,讓鄉(xiāng)村百姓重新了解家鄉(xiāng)��,關注家鄉(xiāng)的環(huán)境和文化變遷����。
“ 這些鄉(xiāng)村拍攝者們能從草根視角,重新審視自己熟悉的生活環(huán)境�����,展現(xiàn)給大家一個個發(fā)展變遷中的鄉(xiāng)村百姓所見所思的真實生活��?��!惫加钫f��。

▲《鄉(xiāng)村婚禮》(攝影/石來)
我們應該拍什么��?
2 0 0 7 年���, 山水自然把攝像機交給西部的村民和牧民��,讓他們自己拍攝紀錄片����,表達對傳統(tǒng)文化的理解�����,“鄉(xiāng)村之眼”影像紀錄項目就此誕生�����,同時�����,“鄉(xiāng)村攝影師”也應運而生��。
7年的時間��,“鄉(xiāng)村之眼”先后在四川“5·12”地震災區(qū)���、青海湖畔、青海和四川年保玉則地區(qū)、四川大熊貓自然遺產(chǎn)地雅安片區(qū)�����、青海三江源地區(qū)�����、云南德欽的卡瓦格博雪山等地舉辦了7期培訓班���,幫助140多名來自青海�����、西藏�����、四川和云南的普通農(nóng)牧民掌握獨立創(chuàng)作影像的方法�����,并提供影像交流平臺����。
2011年6月,“鄉(xiāng)村之眼”公益影像活動在雅安北部寶興縣��、蘆山縣�����、天全縣的四個村開展活動����,12名來自鄉(xiāng)村的攝影師參加了攝影培訓。
培訓第一天��, 鄉(xiāng)村學員們第一次透過相機來觀察他們熟悉的集市生活���。他們帶上自己的相機去捕捉市集上的故事,拍攝了賣肉的攤子����;清理衛(wèi)生的老大爺;一早上生意沒開張��、面容苦悶的商人����;賣鞋賣了一輩子���、最后一天做買賣的老奶奶和她的鋪子;背著爸爸來趕集的一對父子����;默默擦拭西紅柿的賣菜大姐;在集市上喝著小酒擺龍門陣的老人們……
雖然學員們的照片存在構圖不佳����、曝光不當、甚至有時手指頭會因操作不當意外入鏡等毛病����,但那原本亂糟糟、鬧哄哄的鄉(xiāng)村早集�����,在學員們多視角的觀察和記錄下突然變得生機勃勃���?��!班l(xiāng)村之眼”項目負責人呂賓在看完所有學員的照片后不由感嘆, “ 看他們的照片���,比我自己在集市上看到的����,要豐富和有意思多了!”
雅安大熊貓遺產(chǎn)地有什么值得記錄的東西���?除了攝影技術的指導以外�����,圍繞“大熊貓遺產(chǎn)地”拍攝主題的討論貫穿于這次培訓始末�����。
“鄉(xiāng)村之眼�����,是以鄉(xiāng)土的視野來記錄我們的環(huán)境、生活和文化����。我們有鄉(xiāng)土視野嗎?我們?nèi)绾纬尸F(xiàn)鄉(xiāng)土文化����?”
來自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的李春霞老師圍繞學員們的家鄉(xiāng)—大熊貓遺產(chǎn)地��,用生動的講解啟發(fā)鄉(xiāng)村學員們?nèi)绾瓮ㄟ^鄉(xiāng)土視野來講故事����。她說:“一個地區(qū)的文化����,是與這個地區(qū)的土地捆綁在一起的。我們生活在大熊貓家園里���,大熊貓的家����,也是我們的家�����。我們講述的故事���, 就是大熊貓遺產(chǎn)地的故事�����, 就是大熊貓遺產(chǎn)地的文化和遺產(chǎn)����。”
春霞老師啟發(fā)學員討論: 如果拍攝給自己的家人看����,自己會拍些什么內(nèi)容;如果拍攝給外來人看���,又會拍攝些什么內(nèi)容��。
來自天全縣大仁煙村的王顯芬聽后大受啟發(fā)�����,她說:“一想到我拍攝的照片可以讓我的兩個兒子長大后看到����,我就覺得很興奮����。我想讓他們?yōu)樽约旱膵寢尭械津湴?����。?/p>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的冉玉杰老師則準備了很多來自生活的照片����、組圖來展示鄉(xiāng)村生活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細節(jié)?���!恫葮驎贰稄R會》《大肉會》等貼近四川農(nóng)村生活的組圖,帶給鄉(xiāng)村學員們更多啟發(fā)����。大河村的楊世貴說,家鄉(xiāng)擺九大碗的場景和冉老師展示的《大肉會》組圖非常相似�����,自己有信心能拍好自己家鄉(xiāng)的生活了����。
培訓的最后一天,村民們討論起未來拍攝的方向�����。
彭清柏,來自天全縣大仁煙村的村民���。20年前���,做過走村串鄉(xiāng)的鄉(xiāng)村攝影師,為鄉(xiāng)親們拍照片����。平時自己喜歡在家做一些竹藝編制手工藝品。再次拿起照相機��,他說他回家之后��,要去尋找當年那些被他拍過照片的人����,再為他們拍一張照片,拍下他們現(xiàn)在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環(huán)境���。
楊世貴���, 蘆山縣大河村村民�����, 參加過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20年前在部隊時用過相機���,之后就再也沒有接觸過����。他對家鄉(xiāng)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希望通過手中的相機來展現(xiàn)家鄉(xiāng)豐富的自然資源。
來自寶興縣磽磧鄉(xiāng)澤根村的楊明學���,是村上的能人����,他對自己家鄉(xiāng)的鄉(xiāng)土文化�����、傳統(tǒng)習俗���、包括紅軍故事都很了解��,村上的紅白喜事總要找他出面做主持��。他說起在大熊貓交配季節(jié)���,自己上山放羊時�����,曾目睹雄性熊貓打斗的場景�����,真是繪聲繪色���。他說,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和這位“尊貴的鄰居”打交道的機會還有很多,終于有了相機�����,可以好好地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了。

▲《修山》(攝影/王代華)
有生命的泥巴
對12位質(zhì)樸的農(nóng)民而言�����,透過鏡頭來看家鄉(xiāng)��,處處充滿驚喜�����。天全縣大仁煙村的樊翼這樣講述自己的拍攝心路����,“從照片里看���,家鄉(xiāng)的一坨坨泥巴好像都有生命���。”
寶興縣磽磧鄉(xiāng)澤根村的藏族漢子石來從部隊退伍后�����,一邊養(yǎng)牦牛���,一邊經(jīng)營藏家樂����,“雖然210省道要經(jīng)過澤根村,但曉得我們村的人還是太少了��?��!边@個壯實漢子敏銳意識到���,影像記錄活動對宣傳夾金山下的澤根村是一個好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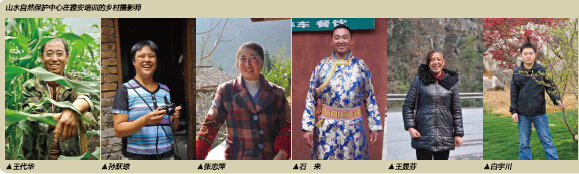

▲《剪牛毛》(攝影/石來)
但是�����,拍什么是一樁難題���?����!皠傞_始偷拍鄰居家的女兒在頭上編花帶子����,緊張得手都在發(fā)抖?��!毙姨澿徏疑倥咔拥卣f把她拍漂亮了�����,石來這才有了底氣���。
一個雨后的清晨���, 石來看到夾金山薄霧輕籠����,放眼處一片碧綠��,于是穿著長筒靴爬到半山腰上����,拍了一張村莊的全景,“照片后來在我們村展出�����,好多人稀奇得很,‘沒想到我們生活的地方����,比電視里的風景區(qū)還漂亮!’”
磽磧鄉(xiāng)每年農(nóng)歷四月中旬都有剪牛毛活動����,以便讓牦牛來年長得更強壯。澤根村幾乎家家都養(yǎng)牛����,牛平時放養(yǎng)在崇山峻嶺中,要把它們趕在一起并剪完牛毛��,差不多要花將近半個月���。為了拍攝剪牛毛的場景����,石來第一次當了“逃兵”��,不再去和生猛的牦牛斗智斗勇��。他拿起相機拍下了牦牛主人姜健文燒柏枝黃紙��、點香燭祈福的全過程,拍下了這位嘉絨漢子在一片奔騰的牦牛群中擒住一頭牛并把它按倒在地的驚險一刻�����。還拍下了給牛喂雞蛋��、清油的照片�����。
石來說���,“即使牦牛只是牲口,我們也會善待它們����。喂它們吃雞蛋,是安撫它們受驚的心靈���,同時恢復體力����?����!彼€拍了主人招呼大家吃包子、發(fā)糖果的照片�����,“我們這里啥都是一起分享����,大家相互幫忙勞累多天,一分錢都不會收�����?��!?/p>
寶興縣蜂桶寨鄉(xiāng)順山村的向興林是村里的會計��,以前從沒摸過相機��,結果這年冬天下大雪�����,家住半山腰的他天亮起床���, 隨手拍了一張《順山村的雪景》�����。照片近處����,白雪掩蓋了一半的玉米地���,遠處的樹木全部披上了銀裝�����。
徒手擒牦牛���、看爺爺編竹籬����、94歲老人的全家福、村民的房屋�����、穿婚紗的農(nóng)家新娘……真實的鄉(xiāng)村生活,像一幅幅畫卷��,讓人震撼����。
在上里古鎮(zhèn)培訓時,樊翼就曾有過感嘆�����,“人家磽磧鄉(xiāng)的藏族同胞���,民族服裝一穿����,照片顏色就巴適得很……”在老師的啟發(fā)下�����,樊翼開始關注山鄉(xiāng)婚喪嫁娶��、留守老人�����,甚至村子里所有農(nóng)戶的房子。有一年春節(jié)����,他一口氣拍了上百張村民在自家房前合影的照片。有人問他合影會不會千篇一律��?這位年輕的農(nóng)民一口答道:“這才是原生態(tài)噻��,農(nóng)民拍照未必還興擺造型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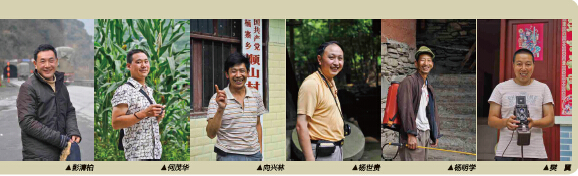

▲《九大碗》(攝影/張忠萍)
王代華是主動申請加入“ 鄉(xiāng)村之眼”活動的�����,他想要記錄當?shù)剞r(nóng)民真實生活狀態(tài)����。他有一張名為《殺獅》的照片, 拍的是澤根村春節(jié)的習俗���, “ 我們這里一般正月初十的時候‘ 殺獅’(燒掉當年春節(jié)期間用竹子和紙編的舞獅)��,表示新年就過完了��。這種習俗好多地方?jīng)]有吧���?”
尋找人與自然的答案
這是一個“拌著泥土氣息”的影像試驗,這些村民生平第一次拿起相機開始拍攝自己的家���,拍攝自己的丈夫��、妻子����、小孩���,拍攝自己以及周圍鄰居們的生活����。石來說:“通過拍攝照片�����,我開始重新學習和了解自己不甚了解的鄉(xiāng)土習俗����?�!?/p>
12位農(nóng)民���,本身就是鄉(xiāng)村鏡頭中的主角,參加拍攝行動后�����,他們漸漸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熟悉的生活���,思考環(huán)境與生態(tài)問題���,產(chǎn)生了從沒有過的思考。
“ 鄉(xiāng)村之眼” 的學員經(jīng)常和郭思宇聊當?shù)匾吧鷦游?����,如山悶墩兒(小熊貓)����、土豬子(豬獾)、娃娃雞(紅腹角雉) ����、彎鼻子( 羚牛) 以及刁靈子(松鼠)等。
順山村的學員張忠萍���,專門拍了一張兒子茍毅和伙伴下河撈魚的照片���,照片里小伙子兩手空空,一無所獲��。張忠萍說���,在附近修水電站以前����,只要拿撮箕到河邊一撮��,就能撮起魚���,“可是電站一修����,河流的水量少了很多����,魚越來越少���。”
樊翼是天全縣紫石鄉(xiāng)大仁煙村的村民����,也是村黨支部書記?����!拔也皇菙z影師���,通過接受培訓����,平時司空見慣的環(huán)境拍成圖片���,比在電視�����、電影�����、掛歷中看到的環(huán)境美多了��?����!彼榻B���,村上與他一起參加山水自然行動的還有村民王顯芬、彭清柏����。通過參加活動,他開始思考著如何運用圖片形式��,引導更多的村民增強自豪感���,使鄉(xiāng)村文化資源成為村民加快發(fā)展的不竭動力��。
12位學員用他們鄉(xiāng)土化的表達�����,記錄著自己質(zhì)樸的自然保護觀�����,表達著他們對人文����、環(huán)境變遷的關注與展望,希望用影像尋找有關人與自然的答案����。
他們發(fā)現(xiàn),在城市化的進程中���,鄉(xiāng)村內(nèi)在的生存狀態(tài)也在悄然生變����。樊翼拍的村里的留守老人�����,孤獨地坐在自家的木板房前���;今日茶馬古道上仍在繼續(xù)行走的背夫��,也被彭清柏定格……
幾年下來�����, 這些鄉(xiāng)村攝影師們拍攝了上萬張照片��,逐漸積累形成了數(shù)十個相對成熟的拍攝主題����。他們在四川雅安�����、成都��,云南大理����、昆明,貴州荔波都舉辦或參加了影展�����,也在每個村里自己組織舉辦了鄉(xiāng)村圖片展。小小的相機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改變���,很多人下地干活����、上山放牛也隨身帶著相機�����,記錄下生活的點滴���。
活動結束了����,拍照的習慣卻被村民保留了下來���。即使扛著鋤頭到自家地里干活�����,藏族漢子石來也不忘帶著自己的數(shù)碼相機�����。妻子揮舞鋤頭勞動時��,他也會在一旁咔嚓咔嚓按下快門���,還不忘提醒妻子“莫要盯到鏡頭笑”���。妻子薩爾中認為他這是不務正業(yè),“哪個農(nóng)民像他那樣拿個相機到處轉(zhuǎn)嘛”���。
2012年8月��,這些村民自發(fā)成立了“雅安山悶墩兒鄉(xiāng)村攝影協(xié)會”(后注冊為雅安市鄉(xiāng)村攝影協(xié)會)�����,繼續(xù)堅持在業(yè)余時間拍攝身邊的真實生活。
“每次整理村民拍攝者的照片����,正是由于他們記錄下的往往是即興的一瞬間的情景,而非刻意的雕琢����,所以在閱讀這些畫面和他們講述的文字記錄的時候����,我們能感受到一種‘隱藏’著的力量��,這也正是這些樸素的照片有別于主流優(yōu)秀攝影作品的特點��,就是告訴你��,‘在那兒��,就是這樣’�����?���!痹凇堆虐泊笮茇堊匀贿z產(chǎn)地影像紀錄行動》圖片集的前言中,郭思宇如是寫道��。
郭思宇認為�����,這些作品的影響力�����,不僅僅只是觀眾出于對“村民”這個標簽而發(fā)出的鼓勵性質(zhì)的掌聲?�!?鄉(xiāng)村之眼”開創(chuàng)了“人與自然關系草根化表達”的嘗試���,讓城市傾聽來自鄉(xiāng)村社區(qū)的聲音����。更重要的是��,這些鄉(xiāng)村影像實現(xiàn)了本地人的自我教育和啟發(fā)���。
2014年1月���,在《南都周刊》主辦的“2 0 1 3中國溫度榜”頒獎典禮上,“鄉(xiāng)村之眼”公益影像計劃項目團隊獲得“最佳團隊獎”���。
“ 鄉(xiāng)村之眼, 用影像啟蒙���, 讓當?shù)厝俗约撼蔀榧o錄片的記錄者和主角���,點滴改變和保護西部傳統(tǒng)生態(tài)�����、文化火種……”主辦方的授獎詞����,點出了“鄉(xiāng)村之眼”的意義和價值�����。
(本文圖片由山水自然保護中心提供�����,特此致謝?�。?/p>
(編輯 郭晨梅)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wǎng)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wǎng)
 不良信息舉報窗口
不良信息舉報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