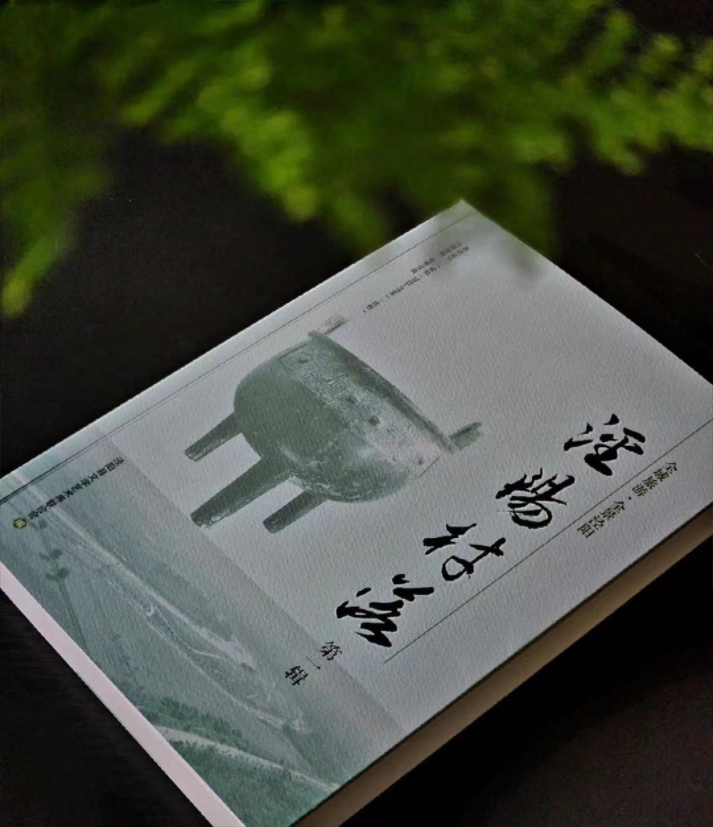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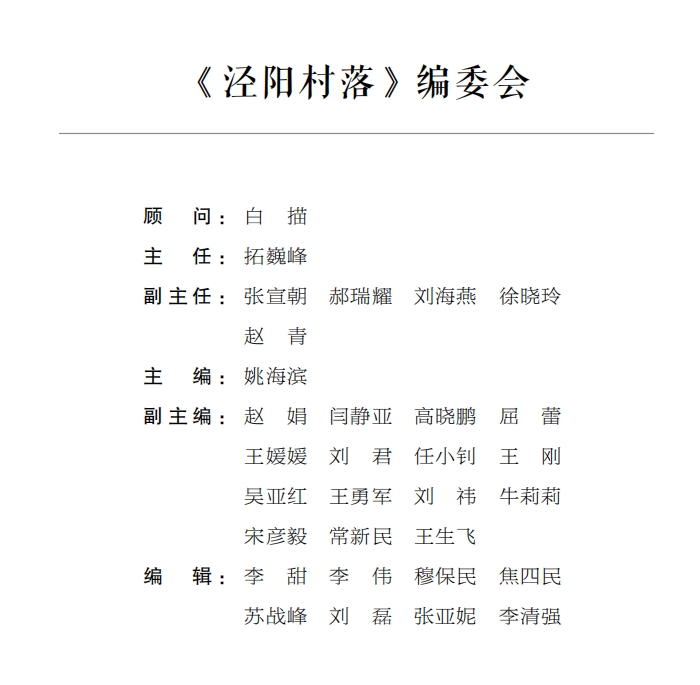
太和村——我的鄉(xiāng)愁
韋良鴻
我的家鄉(xiāng)太和村地處涇陽縣的西北塬上����。因?yàn)橹笆莻€(gè)荒草灘,當(dāng)?shù)厝艘步袨├锎?�。全村人都是清朝末年先后從山東省淄博市周邊逃難來的難民�。當(dāng)年淄博附近連年旱災(zāi),民不聊生��,村民們只能四處逃荒��,太和村村民只是逃荒人群中的一小部分��。大家推著“地轱轆”車��、挑著擔(dān)子一路乞討來到?jīng)荜柕奈鞅避?���,在?dāng)?shù)厝瞬辉父N的荒草灘上定居下來。因?yàn)闆]錢蓋房���,就挖出地坑窯居住��。地坑窯在村里是最常見的“建筑物”�����?!疤汀贝宕迕膩須v可能是,在經(jīng)歷了貧困饑餓和顛沛流離之后�,祖先們憧憬安定富足的生活,便取了紫禁城中最為高大的“太和殿”的名稱作為村名�,以寄托對(duì)子孫后代的美好期望。
村子里以“韋”姓和“魏”姓居多���?�!绊f”姓在山東老家也是大戶����,逃難走的時(shí)候同族的長(zhǎng)輩還讓各路人馬都帶上了輩份排序:“賢孝忠良節(jié)��,福祿壽禎祥����,恭寬信敏惠��,繁衍世澤長(zhǎng)”���。每個(gè)字都蘊(yùn)含著道德和文化的內(nèi)涵�����。一共二十輩���,大約能排四百年�。祖先們希望若干年后子孫后代還能相親相認(rèn)��?!拔骸毙盏奈何髟獊泶謇镒钤纾撬l(fā)現(xiàn)了太和村這塊“風(fēng)水寶地”���,數(shù)次來往陜西山東�����,也算是鄉(xiāng)親們逃難路上的領(lǐng)路人�。他也曾在民國(guó)十八年(1929)年饉時(shí)組織村民到淳化去運(yùn)糧販糧�,讓大家順利度過了饑荒,因而在村民中很有些威信��。他在老家讀過書��,對(duì)“耕讀傳家”的傳統(tǒng)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對(duì)興辦學(xué)校很是熱衷。在他的倡議和主持下��,周圍七八個(gè)村子聯(lián)合起來,在我們村子的中間建起了一所學(xué)校���。
學(xué)校建于三十年代初期���,是每個(gè)家庭出錢、出物�、出力修建的。雖然我們村的村民都是車推肩挑過來的���,生產(chǎn)和生活資料非常匱乏�,但在建學(xué)校時(shí)卻毫不吝嗇���,帶頭出錢出力��,這充分顯示了老一輩人不甘貧窮����、改變命運(yùn)�����、育人為本的深謀遠(yuǎn)慮��。學(xué)校是方圓最高大最堅(jiān)固的建筑���,青磚瓦房����,高大的紅漆大門���,門口有兩個(gè)大石獅子����,剛進(jìn)門兩邊是兩排廂房�����,往里走是一座十多米見方的大教室��,教室里面有四個(gè)粗壯的柱子��,檁條和椽子都非常筆直結(jié)實(shí)����,椽子上邊鋪的是望磚,顯得寬敞大氣、堅(jiān)固耐用���,和村民們住的地坑窯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學(xué)校院子里栽滿了柏樹����,四季常青�。這所學(xué)校承載了學(xué)子們成人成才的夢(mèng)想,也盛滿了我們兒時(shí)的樂趣和笑聲�。學(xué)校在五十年代初期還是“太和鄉(xiāng)”所在地。當(dāng)時(shí)的行政體制是縣—區(qū)—鄉(xiāng)—村��,太和鄉(xiāng)管理了秦宋�����、雙槐�、范李范圍以內(nèi)的所有村子,人民公社以后才撤銷�。
我們村的第一個(gè)特點(diǎn)是怕水。因?yàn)榇遄拥貏?shì)低洼�,夏天如果下暴雨,周圍的雨水就會(huì)聚集到這里來�。之前這里就是洪水的水路��。也正是因?yàn)槿绱耍?dāng)?shù)厝藢幵缸≡谏狡?���、溝畔,也不愿居住在這平灘上來�����。民國(guó)時(shí)期我們村曾經(jīng)發(fā)過好幾次大水����,村里有五六家窯洞被洪水浸泡坍塌,三四個(gè)人被淹死���。我親眼見到的一次洪水發(fā)生在1968年����。那是7月份的一個(gè)晚上��,一場(chǎng)暴雨過后�,從東北方向傳來了巨大的轟鳴聲,有經(jīng)驗(yàn)的村民說是洪水下來了�����。隊(duì)長(zhǎng)立即組織年輕人去開挖洪水通往洪溝的水渠。好多人家立即把糧食和重要物品從窯洞往地面上轉(zhuǎn)移��。因?yàn)闀r(shí)間倉(cāng)促���,糧食也拋灑了不少���。天亮后站在村子向北望去,呀�!白茫茫一片汪洋。再看腳下��,洪水已經(jīng)在窯背上打轉(zhuǎn)轉(zhuǎn)�����,眼看著就要灌進(jìn)窯坑中去了��。有驚無險(xiǎn)�����!因?yàn)榇謇锶思皶r(shí)挖開了洪水的去路��,洪水一路向西流向了洪溝,再?gòu)哪臼釓澚飨驔芑萸?���,直到天快黑時(shí)才流完�。洪水成了太和村人揮之不去的噩夢(mèng)。七十年代中期��,大隊(duì)統(tǒng)一在地勢(shì)較高的“塬上”規(guī)劃了“居民點(diǎn)”����,之后村民們逐漸都搬到了“居民點(diǎn)”居住,再也不怕洪水的肆虐了���。
我們村的第二個(gè)特點(diǎn)是缺水����。既怕水�����,又缺水�,就是這么矛盾。我們居住在盆地的中心卻沒有地下水����,實(shí)在讓人想不通����。最初村民們打了許多井���,打到十幾丈二十丈深��,還不見水的影子�����,只好死了打井的心思����。到白王村去挑水��,挑一擔(dān)水需要一個(gè)多小時(shí)�,還要看人家的臉色。只好打窖存水��,最早是收集雨水�����,后來是儲(chǔ)存黑松林水庫(kù)放下來的渠水。水窖的存儲(chǔ)能力有限����,1975年以后在人口數(shù)量不斷增長(zhǎng)的情況下就不時(shí)地出現(xiàn)水荒。1985年以后由于渠水嚴(yán)重污染無法飲用����,村民被迫每家自備汽油桶到白王去拉水��。八十年代后期���,村上打了深井(200米)���,修了簡(jiǎn)易的水塔,但群眾吃水還得用架子車去拉���,直到九十年代安裝了“篩珠洞”送過來的自來水��,吃水難才得到徹底解決�����。生產(chǎn)隊(duì)時(shí)����,在我們村的西頭和東頭各有一個(gè)大水池,村民們稱為“澇池”�,可以收集打麥場(chǎng)流下來的雨水,也可以儲(chǔ)存渠水���,澇池底下用紅膠泥做了特殊處理�,既能防止?jié)B漏��,又不至于使水體發(fā)臭���,而且還有自動(dòng)凈化的功能����。放一次水能用兩三個(gè)月��?����!皾吵亍痹诋?dāng)時(shí)的情況下發(fā)揮了大作用:一是全村人都在這里洗衣服�����;二是卸套后的耕牛在這里飲水;三是夏天男人們?cè)跐吵叵丛栌斡?�;四是村民澆菜��、和泥(搞建筑)都在這里挑水�。從九十年代后期開始,大家都用上“篩珠洞”的礦泉水�����,水質(zhì)好�����,水量足����,好多人還安裝了“太陽能”����,幾代人“暢快”用水的夢(mèng)想終于變成了現(xiàn)實(shí)。
當(dāng)年的太和村人幾千里沿路乞討而來���,嘗盡了人世間的酸辣苦澀���,但是從來沒被苦難嚇倒����。他們樂觀豁達(dá)�、堅(jiān)毅自信,他們創(chuàng)造了生活���、也享受著生活���。村里的婦女都學(xué)會(huì)了一樣手藝,就是攤煎餅����。這種煎餅不是在鍋里攤的,食材也不是麥子面�,而是用鏊子(中間高四周低的特制鍋)攤的,食材是純玉米面���。在那個(gè)困難的年代���,小麥很稀缺,玉米在口糧中間占到了一大半,經(jīng)常是早晨玉米粥���,下午湯“魚魚”�。但玉米面的口感不好���,于是人們就想著法子“粗糧細(xì)作”����,而鏊子攤的玉米面煎餅就大大改善了玉米面的口感���。要是在制作工藝上再講究一點(diǎn)(把玉米糝泡軟用石磨子磨成糊再發(fā)酵)���,口感就更勁道。如果把當(dāng)天攤的煎餅放到第二天��,再放到鍋里烙一下���,吃起來和白面鍋盔一個(gè)味。我們村的兩個(gè)技術(shù)能手還曾經(jīng)到白王的機(jī)關(guān)灶房進(jìn)行過展示���,受到了大家的熱烈歡迎�����。攤煎餅是個(gè)技術(shù)活兒����。用鐵勺舀一勺面糊倒在鏊子中間,再用木質(zhì)耙子轉(zhuǎn)著圈把面糊均勻地?cái)傞_�����,技術(shù)越高就攤得越薄�����,口感也就越好��。要點(diǎn)是:第一�����,做到受熱均勻���。鏊子離地面只有不到十厘米�����,一般都用麥秸燒火����,添柴時(shí)要在鏊子底下完全鋪開。第二�����,面糊攤開時(shí)既要盡可能地?cái)偙?���,又不能出現(xiàn)漏洞。如果攤得厚或者打補(bǔ)丁�����,都會(huì)影響口感����。第三,揭煎餅時(shí)用力要均勻���,既要把煎餅揭下來,又不能把餅扯爛�。從山東過來的婦女都會(huì)攤,本地嫁過來的媳婦就一茬接一茬地學(xué)習(xí)。一到冬天��,家家戶戶都支起了鏊子��,煎餅的香味就彌漫了整個(gè)村子�����。
男人們的一項(xiàng)絕活就是蓋草房�����。提起蓋房子����,人們首先想到的建筑材料就是磚和瓦,但我們村子的人不用一磚一瓦也能蓋房�����,就是蓋草房��。草房的墻是用泥土夯成的�,木料的使用量不到瓦房的五分之一,房頂上的覆蓋物是麥草��。草房的椽是橫擺在山墻上的,在椽的上面豎著用高粱稈或玉米稈織成籬笆���,在籬笆上抹上泥�,再把麥草固定在泥巴上��。蓋草房的核心技術(shù)就是上麥草�����,上草的時(shí)候用木板搭在兩根椽之間����,人蹲在木板上作業(yè),一層麥草一層泥����,用泥把所有的麥草都固定起來。上草要做到順溜整齊�����、均勻扎實(shí)����,沒空隙�、沒亂草����。還有的人家專門在山里割了一種叫“雞更更”的野草回來蓋房子��,效果比麥草更好�����。草房的坡比瓦房要大���,有利于雨水快速流下����。麥草雖然不值錢��,但是雨淋不透�、太陽曬不透,防水隔熱效果非常好����,是真正的冬暖夏涼。我們村生產(chǎn)隊(duì)時(shí)的飼養(yǎng)室和庫(kù)房都是草房�����,有二十多間,還有幾戶 家境“殷實(shí)”的人家也蓋了草房�,草房的造價(jià)不到瓦房的十分之一, 是真正的經(jīng)濟(jì)實(shí)惠�,但在那個(gè)年代還是奢侈品呢!

▲焦四民/畫
太和村的耕地面積有限�����,加之大部分都是些壚土地��,產(chǎn)的糧食不夠吃�����。壚土地土質(zhì)堅(jiān)硬���,容易板結(jié)�,保墑保肥效果差�����,糧食產(chǎn)量比同等的黃土地要低出百分之二十�����。為了填飽肚子,我們的祖先想出一個(gè)好辦法����,大家徒步三四十里山路�����,來到北仲山里的“刺咀”�����,在大山深處安營(yíng)扎寨�����,開出大片的荒地���,種下土豆和谷子���。雖說是山坡地,但山里夏天氣溫低��,土地涼,水分消耗少���,適合土豆和谷子的生長(zhǎng)�����。到了秋季��,男女老少背著口袋�����,滿載而歸�����。在那廣種薄收的年代�,“靠山吃山”算是解決了一個(gè)大問題���。在農(nóng)閑時(shí)節(jié)����,男人們還從山里割回“條子”,有榆木的��,有桃木的��,能編出籠���、筐�、背 簍等生產(chǎn)用具�,多余的還能拿到集市上換些零花錢。
太和村村民繼承了山東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他們吃苦耐勞��、坦誠(chéng) 正直�、豪爽豁達(dá)��、不怕困難����,也融合了陜西人的文明、細(xì)致和儀式感�����,形成了自己的獨(dú)特風(fēng)格。一百多年過去了�,人口也繁衍了五六輩,生活條件和村容村貌也都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太和村卻一直保存著自己的獨(dú)特傳統(tǒng)和文化��,這已經(jīng)成為太和村的民風(fēng)民俗�。而這種文化基因也在洗禮著太和村的一代又一代人�����,使他們陽光上進(jìn)�����,成人成才���!
太和村��,你是地坑窯里的冬暖夏涼����;你是老學(xué)校里的啊喔衣烏;你是爺爺油燈下編織背簍的背影�����;你是母親手里熱騰騰的煎餅����;你是壚土地上的犁耬和耙耱;你是祖先們抗?fàn)幟\(yùn)的“地轱轆”車���!
太和村����,我的鄉(xiāng)愁���!
作者簡(jiǎn)介
韋良鴻,中學(xué)高級(jí)語文教師�。興隆鎮(zhèn)太和村人,生于1958年12月���,曾在白王���、王橋任教三十六載。如今退休在家,回憶往事��,寄情家鄉(xiāng)�、書寫幽懷,以饗父老鄉(xiāng)親��。
(本文選自涇陽縣文學(xué)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huì)2022年10月編輯出版的《涇陽村落》第一輯)
責(zé)任編輯:王順利/《新西部》雜志 · 新西部網(wǎng)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wǎng)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wǎng)
 不良信息舉報(bào)窗口
不良信息舉報(bào)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