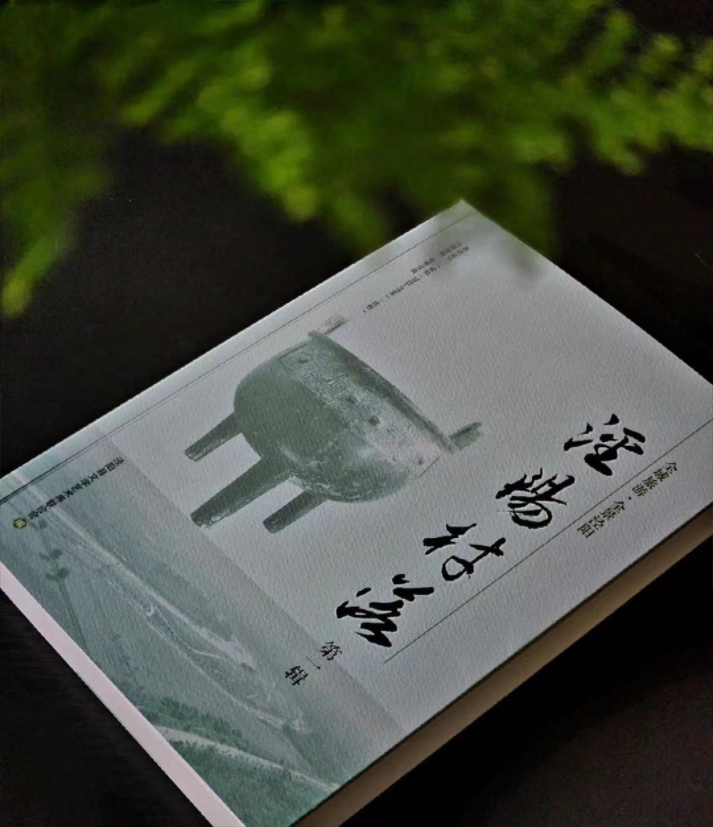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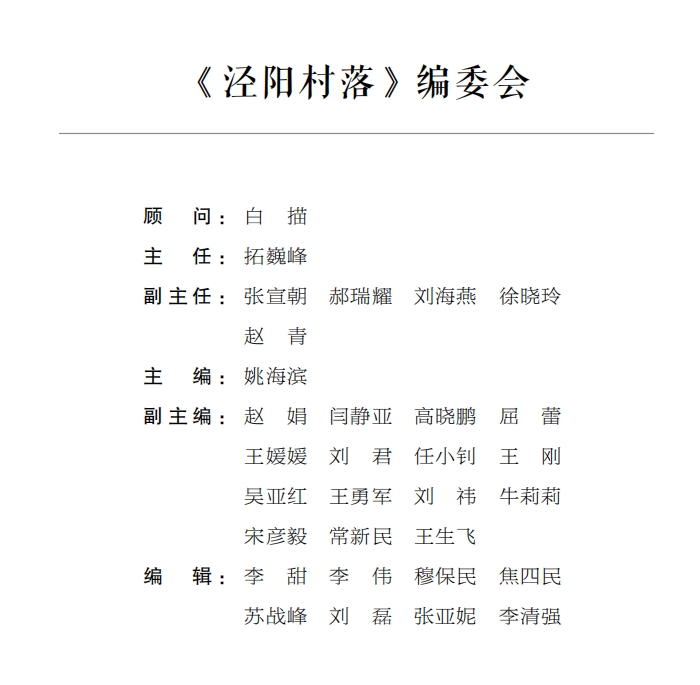
沙溝�,一個(gè)遠(yuǎn)去的村落
文/吳錫宏
沙溝,一個(gè)在撤鄉(xiāng)并鎮(zhèn)中早已遠(yuǎn)去的村落��,但記憶中�����,那縷縷從家家戶戶院子里升起的炊煙���,溝內(nèi)���,不時(shí)傳來(lái)剛剛產(chǎn)完蛋母雞的歡歌聲,走在下地干活路上牛兒“哞哞”的撒嬌聲�����,和那些飛奔出圈羊兒們“咩咩”的歌唱聲�。溝里,那隱隱約約回蕩著的母親呼喚兒子吃飯的聲音����,更是將自己的思緒又拽回到了那些難忘的過(guò)去。
沙溝是唐崇陵山下最長(zhǎng)的一條溝,南北長(zhǎng)約四公里����,以前,大家都依溝挖掘窯洞而居�,因溝內(nèi)出產(chǎn)大顆粒沙子,所以取名“沙溝”�。
我家就在南端溝口的右側(cè),朦朦朧朧的還記得����,在家門口東邊大約不到一千米的地方,曾經(jīng)有兩行自南到北�,長(zhǎng)約八九百米長(zhǎng)的石豬、石羊和兩個(gè)高高的石柱�����,后來(lái)才聽(tīng)村里老人說(shuō)����,唐朝的一位公主葬在附近����。
過(guò)去農(nóng)村人吃飯喜歡蹲在門外,當(dāng)時(shí),我家門口可是有全村獨(dú)一無(wú)二的天賜之物�。在大門口右邊,有兩個(gè)高出地面一尺多的圓形拴馬樁�,成了我家門口一對(duì)天然的石凳 ; 在大門口的兩側(cè),分別站立著一棵需要兩人才能合抱的大槐樹(shù)�,村里人都叫它“看莊槐”。正因頭頂有兩棵大槐樹(shù)的護(hù)佑���,地上有天然石凳賜坐�,一年四季���,無(wú)論刮風(fēng)還是下雨�����,坐在家門口���,總給人一種舒適、安全的感覺(jué)��。

▲唐崇陵
過(guò)去村里有多少人沒(méi)算過(guò)�����,也不知道,只是一直記得�����,父母時(shí)常告誡我們 : 言��、行�����、走一定要向大戶人家孩子學(xué)習(xí)����,坐有坐樣、站有站樣�,見(jiàn)人要打招呼,要懂禮貌����。后來(lái)長(zhǎng)大后才明白,偌大個(gè)村里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人��,一類是一直都生活在這里的本地人家�����,另一類就是從外邊遷居來(lái)的客戶人�。由于出生成長(zhǎng)地方不同,一些風(fēng)俗習(xí)慣還真是有點(diǎn)區(qū)別�����。譬如過(guò)年����,村里本地人都講究過(guò)初一,而客戶人都過(guò)三十���,我家隔壁��,一直延續(xù)著每年三十晚上過(guò)年的習(xí)慣���。
雖說(shuō)人群的習(xí)慣略有不同,但是并沒(méi)有影響鄰里之間融洽地相處�,而且還留下了許許多多鄰里互敬互幫的佳話。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親和他的干哥的故事����。
在村里�,甚至鄰村����,凡是晚一輩的人都將父親叫“五叔”,我始終就想不明白�����,我家姓吳���,不叫吳叔為何要叫五叔呢���?為這事還糾結(jié)了好多年,一直到初中快畢業(yè)����,問(wèn)母親才知道,當(dāng)年父親十二歲時(shí)�����,一個(gè)人跑到了沙溝��,認(rèn)識(shí)了這里徐家的老二����,他倆還真是有緣,不久就拜了八字��,成了干兄弟�����,按照過(guò)去人的講究�����,干兄弟就是親兄弟���,只是姓氏不同而已��,當(dāng)時(shí)徐家共有親弟兄四人���,父親年齡都比人家小,順其自然就排行在老五的位置���,就這樣�,父親成了村院中晚輩們公認(rèn)的五叔啦���!
由于當(dāng)初父親只有十二歲�,還只是個(gè)孩子。自從有了這一幫鐵弟兄陪伴后���,慢慢就有了依依不舍的感覺(jué)�。后來(lái)�����,干脆在大家慫恿下�,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父親,竟膽大地和干哥一起找保人擔(dān)保買地��,借棉花�����、以物抵債買宅院�,一步一步,稀里糊涂就成了地地道道沙溝人�。可以說(shuō)�����,沒(méi)有當(dāng)初徐家二伯和那幫老輩們的幫扶,就不會(huì)有今天我們的一家�����!
這里不但人好�����,而且在民間還有許多神話般的傳說(shuō)��。
相傳�,當(dāng)年德宗陵朱雀門前的那對(duì)翼馬饑餓難忍�,夜間便偷偷跑到附近玉米地里偷吃,玉米被糟蹋很快讓村民發(fā)現(xiàn)���,大家立即自發(fā)拿起馬刀�����、鐵矛��、鐵叉等工具�,夜間提前埋伏����,守株待兔�,當(dāng)那對(duì)翼馬再次走進(jìn)玉米地�,被埋伏的村民用長(zhǎng)矛刺傷了脖子。從那以后���,地里玉米安全了�����,可是�����,突然有人發(fā)現(xiàn)���,朱雀門前那對(duì)威武翼馬脖子下方出現(xiàn)了斑斑血跡。
這時(shí)�,有民間得道的高人說(shuō),這是唐王陵沒(méi)人祭祀����,沒(méi)了祭品,神馬饑餓難忍,沒(méi)辦法才偷偷跑出去吃玉米充饑���,真是造孽呀����!被傷成這樣���!這樣一說(shuō)�,嚇得那晚參加圍剿的村民仔細(xì)一想����,還真是�,那晚的確是用長(zhǎng)矛刺傷了馬脖子,村民們?cè)较朐脚?����,就匆忙帶上祭品�,跑到神馬面前,祈求神的原諒����。從這件事后,每逢重要日子,或者家里有不順心事情的�,都會(huì)有人來(lái)石馬前虔誠(chéng)祭祀祈福。慢慢地�����,原本的朱雀門�,在眾人一傳十、十傳百中就叫成了“石馬行”����。傳說(shuō)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這對(duì)翼馬脖子下的血跡至今依然清晰可見(jiàn)����。
俗話說(shuō) :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情��。我們居住的這條溝雖然偏僻����,但還真算得上是一方紅色故土�����。村里不僅有曾經(jīng)參加過(guò)榆林戰(zhàn)役�����,戰(zhàn)傷一只眼睛的老兵����,有抗美援朝的老軍人�����,更有一直默默為革命付出的交通員���。
小時(shí)候,村里鐵匠鋪的秦七爺有次逗我們幾個(gè)孩子玩時(shí)說(shuō)�,別看七爺現(xiàn)在是打鐵的,年輕時(shí)候七爺可牛啦�!手里一桿破牛腿槍,指哪兒就能打哪兒�,只要能看見(jiàn)來(lái)人影子,說(shuō)打你左腿膝蓋��,絕不可能打到大腿上。他說(shuō)��,那時(shí)凡是從淳化翻越嵯峨山�����,經(jīng)過(guò)我們村子這條交通線的共產(chǎn)黨人����,都是由他親自負(fù)責(zé)接送,更了不得的是���,他護(hù)送的人員中�,有一位就是廣播里常說(shuō)的一位中央首長(zhǎng)�����,由于保密原因�����,他就是不說(shuō)到底是誰(shuí)�����。神呀!七爺還護(hù)送過(guò)中央領(lǐng)導(dǎo)���。我很懷疑七爺?shù)恼f(shuō)法����,回家就問(wèn)父親是不是真的����。父親說(shuō),估計(jì)是真的��,因?yàn)楦赣H在這兒不遠(yuǎn)處讀小學(xué)時(shí)���,他的老師就是地下黨��,當(dāng)時(shí)誰(shuí)也不知道�����,直到解放后,老師隨組織和隊(duì)伍走了�,大家才知道他原來(lái)是一名地下黨員。
后來(lái)�,一個(gè)偶然機(jī)會(huì)����,我遇到一位老政協(xié)委員���,聊天中得知����,原來(lái)他家解放前是黨組織的一個(gè)秘密聯(lián)絡(luò)點(diǎn)����,他也多次參與過(guò)信息傳遞和人員護(hù)送工作。當(dāng)我剛要開(kāi)口問(wèn)秦七爺時(shí)�,老政協(xié)嘆息地說(shuō) :你村里老七真是好人呀!不但槍法好����,而且護(hù)送人員工作從未出過(guò)差錯(cuò),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從老政協(xié)發(fā)自心底的夸贊聲中�,一個(gè)深藏不露、不居功自傲的七爺形象瞬間被定格在我的心里����。
至今清晰記得�����,1978 年 8 月 3 日夜里�,村子突降暴雨��,山洪暴發(fā)���,溝內(nèi)兩道攔水大壩接連決堤��,村子瞬間被突然涌來(lái)的巨浪淹沒(méi)�,后來(lái)村子整體搬遷進(jìn)了新建的泥瓦房��。隨著改革開(kāi)放��,泥瓦房又轉(zhuǎn)瞬消失�,拔地而起的是一棟棟高低錯(cuò)落的小洋樓,一條條街道綠樹(shù)成蔭��,一個(gè)個(gè)門前花園形態(tài)各異���,繁花似錦��。祭祖日子的街道�、門前�,小貨車、面包車��、各式的小轎車更是鱗次櫛比�。
當(dāng)我回到曾經(jīng)是老宅的地方,遠(yuǎn)遠(yuǎn)向我招手的唯有那兩棵見(jiàn)證了百年沙溝變遷的古槐�,踏進(jìn)已成為耕地的老宅,一股熟悉的泥土芬芳沁人心脾��。坐在大槐樹(shù)下����,家鄉(xiāng)土地散發(fā)出的那股清涼、清靜讓人倍感舒心���??粗矍耙黄f稼���,仿佛聽(tīng)到大槐樹(shù)葉嘩啦啦地對(duì)我說(shuō)��,退休了就趕快回來(lái)吧�����,家鄉(xiāng)的振興還需要你們的余熱���,還需要你們來(lái)搭起現(xiàn)代文明城市與古樸�、自然��、美麗鄉(xiāng)村的橋梁���。
作者簡(jiǎn)介
吳錫宏 , 男�����,1968年8月出生于陜西涇陽(yáng)��。從小喜歡閱讀���,中學(xué)時(shí)曾在《少年文史報(bào)》發(fā)表過(guò)短文,后在《絲路都市文化匯》發(fā)表過(guò)散文《五十年的第一次擁抱》����,在《秦川文化》發(fā)表過(guò)散文《從一次點(diǎn)贊再次感受團(tuán)隊(duì)的力量》等作品�。
(本文選自涇陽(yáng)縣文學(xué)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huì)2022年10月編輯出版的《涇陽(yáng)村落》第一輯)
責(zé)任編輯:王順利/《新西部》雜志 · 新西部網(wǎng)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wǎng)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wǎng)
 不良信息舉報(bào)窗口
不良信息舉報(bào)窗口



